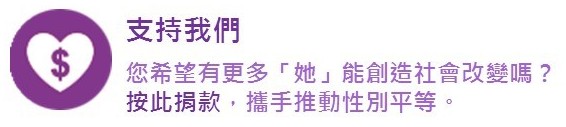陰陽師阿竺:學習性別平等就係學做人
灰白的長髮和羊咩鬚配上瘦長的身形,滿手銀器、指環,加上面容清癯,雙目炯炯有神的資深社工阿竺活像夢枕獏筆下的陰陽師。

小說中,陰陽師認為世上的「咒」皆源於「名」,舉凡人、事、物,有「名」者皆受「咒」所束縛。現實中,擅長思辯的阿竺在過去廿多年一直透過社會工作為弱勢群體「解咒」:為被「污名化」的青年人解咒,以及最近,透過成為 HER Fund 的月捐者,為被社會定型和標籤的女性群體解咒。
「我字典裡面唔會好二元咁去界定所謂男女性特質。嗰啲男人係 Mars (火星)、女人係 Venus (水星) 嘅講法,都會社會上嘅文化定型。」
簡單的二元分法,從來不是阿竺那杯茶。同性愛就等於「不道德」?性工作者就是「不知廉恥」?跨性別人士就是「變態」?理性睿智的阿竺很難接受這一套。
「性別身份係浮動嘅,係冇咁定型嘅。」這是阿竺的性別哲學。
因為不會輕易按照過去一鱗半爪的經驗而蓋棺論定,所以總能引發更深刻的思考。這套雙迴路學習法(double-loop learning)說來可以很複雜,但對阿竺而言這不過是「阿媽醫病」的一套務實哲學。
阿竺母親曾習武學醫,後來在一間醫館幫街坊診症。曾有人因腰痛而求醫,經多次治療情況未見改善。竺媽媽想起有親戚亦被類似徵狀所困,最後發現原來是有患有膽石。
竺媽媽於是致電病人,警告他「應該唔係扭親,係膽石」,著後者去照X光片,事實証明她判斷正確。然而當小小阿竺對母親佩服得五體投地時,後者卻陷入了沉思。
「佢反省,話自己唔啱,唔應該咁講,唔可以咁武斷話係膽石。可能病人係個腎出問題呢?」
學術上,這種態度叫具批判性的省思(critical reflection),但借甄子丹在《葉問2》的講法,這叫「中國人嘅謙遜」。「正因為佢〔母親〕冇讀過好多書,亦唔係正宗學醫... 所以明白偶然性嘅講啱都係有問題,人唔應該咁武斷嘅。」
這套原則一直影響阿竺做人處事,不論是教書還是做社工,他也不會輕易為一些性別問題或現象定名定性。
像男人習以為常地取笑女性司機,認為女人揸車不知所謂,阿竺對此說法就很不以為然。
「一般嚟講,女性操作機械嘅特性同男性係有啲唔同嘅;只不過現時有八成以上嘅道路使用者都係雄性動物,遇到女性司機嗰陣就唔明白佢地嘅狀態。我諗如果有一日路面上有一半以上係女司機,狀況可能會唔同。」
所謂女性不擅操作機械,不過是一些根深柢固的性別偏見。舉例說,男人司機一見人打燈便會下意識地踩油加速,就是有一份「唔想輸俾你」的血氣;相反,很多女性司機會選擇慢下來讓對方過線。這是駕駛風格上的不同,無關好壞。
「其實每個人心裡面都有個巨人。男性嘅巨人係唔可以跌倒嘅,而女性嘅巨人係可以跌倒、可以休息嘅。」
僵化的性別觀念,逼迫的又何止是弱勢婦女和邊緣性小眾?在香港,男士可以表達情感的機會可謂乏善可陳。「男人係唔容易承認自己有痛苦嘅,以前〔年少時〕未有能力表達,成長後社會又唔鼓勵表達。」
壓抑下的情緒,轉化成對「他者」(異性、性小眾)的憤懣和偏見,所謂「咒」,就是如此把我們的世界束縛起來吧?
阿竺承認,自己生命中也有一些不能承受的痛,如十年前左右雙親離逝,這份痛直到此刻他仍在處理,是個非常「有血有肉」的過程。
但亦是因為這份深沉的痛,令人可在無常中抵抗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」,並更能體會到潛藏在人性深處的偉大和侷限。
「我接受呢種狀態,因為咁親嘅人離開,如果去到冇感覺,係好冇人性嘅事。笛卡兒話我思故我在,感受痛苦就係 being(存在)。」
「這份痛告訴我,我還是一個人。」